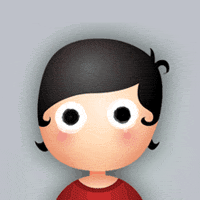《美人册》之七
小来姑娘(下)
20
火车晚点三分半钟,车站却没报。
她穿一身淡绿淡粉相间的运动服,耐克鞋。“这是我实习的报社的同事。”她指着一个挺精神的小伙,“这次来北京是随川剧团采访。”
“我以为你是来专程采访我的呢。”
她瞪了我一眼,斜斜旁边的同事:“别胡说。”又对她同事介绍,“这是斯健,我的亲戚。”
出站时,她犹豫地看着我:“我也可以去住招待所。”头四个字说得较慢。
我没说话,悄悄抓起她的手放在我的风衣兜里。在兜里,两只手相握。我估计她同事不会再回头了,便摸了一下她的腹,“是为这里的事来的吗?”
“讨厌。你想得美。”
要了辆十块钱的破面包车。
“小来,也可以要皇冠车,但下了豪华车进我那个小破屋特没过度。你千万做好思想准备:我那小屋可比我这人破多了。”
“真的?你这人有多破呢?”
“百孔千‘窗’。”我指指她带的网兜。
“那你不成鱼网了?”小来笑得趴在我怀里。
“对喽,要破就破成鱼网。破了两三个洞的衣服不值钱的。可我破到头了,物极必反,倒成了有用的东西了——这不?刚网着条小母鱼儿。”
小来挣脱出身子。她望着车窗外的广场。正是黄昏,华灯未上。纪念碑只有一个轮廊,像被砍掉所有枝杈的大树主干。广场上稀稀疏疏的人影,像风中摇动的小草。
“是缅怀革命烈士吗?”我转过她的脸:上面有一双茫然的眼睛。
“怎么办呢?我父母要知道我跟你的事非得气死——更别说你有老婆了。”
“你想去美国吗?”
“没意思。”她看了一眼旁边的自行车流,“可是不去也没意思。嫁人没意思,不嫁也没意思。”
我亲她一下:“那我呢?”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没有笑。
21
“九点了,电报大楼刚打了九下钟。”我把小来往怀里拢拢,“喝么?小来,——嘿,你披上点儿衣服,别冻着。”她摸出一个紫红的药片塞到嘴里,“你一会儿真得回老婆那儿啊?我要知道这样,我才不跟你——”
“别生气,你现在闭上眼,等你睡着了我再走;明早你别急着醒,你醒的时候我保证也躺在这呢。”
她点燃了烟,我俩轮流抽,烟则由她夹着。
“来,抽你手指夹的烟味道特好,好像这里有你身上的香味。你看过《香水》么?一本德国小说,专讲采集女人身上的香气。”
“你采过多少?”
“我这是头一次。真的。以前那些女孩儿都不抽烟。”我把她吸进的最后一口烟从她嘴里吸出来。
“这么说,都是她们采你了。”
“我身上可没香气,只有萝卜气。”
“你跟吉怎么那么爱吃萝卜呀?”
“可能是命俗,跟萝卜特般配。俗话说:有钱的吃参,没钱的吃萝卜。可是你让有钱的人吃萝卜,他会觉得跌份,觉得那萝卜嗝萝卜屁又贱又臭。可穷人呢?万一要买根人参肯定高兴——又补身子又长身份,肯定不会受到心理挫伤。所以,我觉得人,应从俗做起。文化像翅膀,是人为地添上去的;腿才是咱们的基本,踩到大地上才是自然。当然,如果我们的头脑是雅,也应尽量靠近太阳、星星、蒙画家、舒钢琴家什么的。”
小来歪着头:“这么说你是‘立地’的,我是‘顶天’的?”
“所以,我的头应该往上长,你的腿应往下长。咱们接起来正好顶天立地,是不是跟我在一起特舒坦?可是咱俩一分开就都又极端了。好在走的人容易,飞的人难。比如:我的脚挨一枪,还可以瘸着走,甚至可以爬;你的翅膀挨一枪你能瘸着飞么?子弹没打死你却掉下来摔死了。”
“斯健,你从哪弄来的这些奇怪的理论?”
“其实有时我也不知应怎么活。俗,有时也真让人不甘心——谁让人胳肢窝那长着一些毛毛,跟要长出羽毛翅膀似的。”说着我伸过手去。
“唉哟,别揪,别揪——我不要长翅膀。你这人总没正经。”
“也是,我今晚讲的可能不特俗,可这被窝里哪是讲台呢?还是俗了,对不起——我真的该走了。把腿拿开——嘿,别,别——咱们两情长久,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小来猛地把身子转向墙里:“要滚就快滚。”她的身子抽搐起来,被子也没挡住她那种颤动。
我硬转过她的脸。她嘴唇左右很咸。我帮她把被子掖好,又往录音机里放了一盘舒曼的弦乐四重奏,要不就是三重奏。
“再见,我喜欢你。真的。”
22
“小来,你看,这儿就是法海寺。”我指着山林中的一座古刹,“你等我会儿,我去买点儿萝卜、啤酒,呆会儿得爬山呢。我要看看你的腿在山上有劲没劲——跟我这儿倒是挺有劲儿的。”
小来踢我一脚:“一天不吃萝卜,不说难听的话你就活不了是不是?不许买萝卜,省得撑出你那些乌七八糟的声音。”
这里已是平原的边缘了,往北往西都是山。正是深秋,路两边的杨树叶又黄又皱,落在地上,溅出枯燥的声音。可山上还有丛丛墨绿,环绕着那座古刹。
“这叫什么山?”小来喘着气问。
“翠微山。你没看都这季节了,山上还有绿色。你有什么心愿吗,呆会儿进去许许,让菩萨批准一下。”
“我最不爱进庙了——里边总有一些做作的虔诚。”
“难说。很多半路出家的尼姑,出家前都不爱进庙。你能担保这辈子不会出家?”
“你呢?”她斜眼看着我,笑了,“你出我就出。”
“哟,你那么爱我哪?是不是我一出家你才能看破红尘。我是因为看破红尘才不出的。俗世俗生,现实主义吧。”说着,我去抱她。
“讨厌。庙门口了,别。”她挡着。
“没事儿,这里没和尚,。”
“斯健,要是一个姑娘都不理你了,你怎么办?”
“我也不知道。现在紫禁城里也不需要太监了。没准我也该画画了,专画蒙克那种风格。据说老蒙在女人那儿就特不幸。断了女人的男人都特有创造力。对了,这庙听说就是一明朝的太监修的。”我说。
“咱们不进去了吧?直接上山。你这种人进庙也是亵渎。”小来一边把风衣脱去。
我们走在盘山的小路上,两边都是长势怪异的松柏,有的歪斜,有的扭曲。小来打量着,有时还上去摸摸。
“是不是跟摸到自己灵魂似的?”我拍着她的肩,“是不是特不俗,也特累?”
“斯健,有时我也挺放松的。你正是在我放松的那几天来的成都。可是你走后,我反而觉得更累。我怎么会喜欢你这种‘死皮’呢?按说‘死皮’是不会喜欢‘死皮’的。”
“咱不说这些,咱们今天主要是放松。你看这林子多好啊,”我挽过她的腰,“这么启发人想像力的怪松,你看那棵像不像两个人扭在一起,咱们学学‘他们’。”
小来伸手捂住我的眼睛:“你长的是什么眼睛啊?什么好东西让你一看见也就完蛋了。”
我从她的指缝看见隐约的阳光和橙红的肉色,“你的手特美,”我把她的手拉到我的嘴上,又顶着那只手去够她的嘴,她把手撤去了。
爬上一个山坡,见到一条废弃的公路,除了车辙都长满野草。我俩各走着一条车辙,“咱们这样手拉手并排走,多像儿童下学呀?”她满脸阳光地说。
裤腿蹭着车辙边的野草,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,我吹着一种“平嘴型”的口哨,模仿舒曼的一个旋律——总错,改“罗梦湖”了。小来也不说话,看着路消失的那个山口,时而侧头看我。她的脸微红,很放松。我靠过去,走在两辙之间的野草上,把手挽着她:“小来,是不是?咱俩好像要奔一个好地方去似的——你看前面那山梁,那就是国界,翻过去咱们就该在那边种地生孩子了。”
“你别做诗了。还种地呢?是不是又种萝卜?”
“你这下算理解我了。‘种一地萝卜,养一炕孩子’,桃花源不也就这样吗?”
小来大笑,一边往后拢拢头发:“这么走山路特放松,好久没这样了。”
她使劲看我。我故意把领口拉下,露出胸脯:“用不用我脱了?是不是?小来,我特别奇怪吧?”说着我把她拉上一条林中小路,“咱们该从这儿下山了,走一个小时就是八大处公园。”这的林中依然幽静,我们找了块大石头,靠着休息,喝啤酒。透过树端的阳光在那块石上悄悄挪着。“小来,你往那边挪挪,我这晒不着了。”
她躺着没动,看着天,“你不会到我左边来?我这么躺着感觉特好。”
“好吧,咱别破坏了您的意境。”我就势来个侧滚翻,一下滚在她身上,顺便扫了她的嘴唇,又一个侧滚,落在她的左侧。
“你怎么这么坏呀?”她抬一下头让我把臂重伸进去,“什么好姑娘跟你在一起也得学坏了。”
“学坏了特幸福吧?我就愿意有福同享。”
呆了一会儿,她也落在阴影里了。她坏笑一下也那么侧滚翻。还没等她从我身上翻下去,我抱紧了她,“你可以居高临下地亲我了。”
她身上都有点儿颤了。
“干什么你要?不行,这儿不行。”她拨开俩人身体之间的手。
“多好的环境呀:奇松异石,还有正宗的阳光——非得在小破屋才行呀?这林子里,阴阳之气特补人——你真不懂‘道’。”
“哪有这样的,我——”,她的声音已经有些软绵了,“我怕有人——”
“你不说今天要放松吗。咱们今天学学老祖宗的样子。”
“什么?”她问。
“就是猴子。”
她眼中露出了那种我熟悉的蒙蒙之光。
23
“跟斯健玩这么些天了,还不吃萝卜哪?”吉把递小来的萝卜转给我。
“姑娘吃萝卜确实不雅,就是想吃也得克制点儿。”我瞟瞟小来,“反正我也不特喜欢叼着萝卜的娘们儿——不如像小来那么叼着烟显得深刻又潇洒。”
小央过来给大家倒茶,挺严肃,不跟小来说话。小来眼睛看着在开水中翻滚的茶叶,吸一口烟,烟雾和茶水泛起的水汽融在一起。
“小央,呆会儿你买菜去再买点水果。”吉又转过脸,“小来,斯健给你写过诗吗?”
“没有。就是写了我也不看。他还能写出好话。”
吉往小来的杯中续了几毫升水——她还没喝呢。吉停顿好几秒:“小来,斯健和我都喜欢嘲讽人,更爱自嘲。无非就是把过了时的认真、不成熟的虚伪,都亮出来,摆弄摆弄。沉重和虚伪一样,都是最坑人的。”吉看着我,往上挑着眼睛。
“没错。把自己划在俗人的圈子里便规定了最坏也不过如此的范围。俗就成了根据地,至少可以赖在这儿,如果还有余力再把它用来关心形而上的东西,就会不累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还不停地写东西呢?”她问。
“咱就干这个熟练一些,当然想以此谋生了。写的东西也是以俗为主,就算谁看出雅,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”
吉接道:“很多作家的社会作用跟创作动机都是有距离的。比如小来喜欢的蒙克,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精神的深层恐慌,艺术地总结了性和死亡对人的异化,可蒙克当初是怀有这种动机吗?我只知他是一个十分不幸的人,他若不把这种不幸表达出来,他就会觉得更不幸了。”吉点着头,好像对刚编的这段话挺满意。
“所以,”我总结道,“自己最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;干那种不干就不快乐的事;。如果你是个雅人,再怎么俗你骨子里也变不了;反之也一样。我们所能选择的是:抛弃捡来或学来的深刻;只有轻松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。”我又用眼神把接力棒传给吉。
“小来,”吉赶紧把萝卜咽下去,“我知道你尽跟成都的一些哲学家、诗人深聊;还真不如练练田径、谈谈恋爱、读读有情趣的书呢。我看你这两天比在成都笑的多。”
小来忽然站起来:“好哇,我说你俩今天怎么这么认真,是故意合起来教育我呀——我不听,我帮小央做饭去。”她一转身,见小央依着门框,正朝她微笑呢。
“很好,她以下厨房作为走出深刻的开始了。吉,你听,她俩在厨房说啥呢。”
厨房欢快的锅勺之声。
“咱俩今天真有点儿无聊。你把我也拉进来了,还让我主侃——”吉说。
“小来也喜欢你,这不正让你显示风格吗?”
“饶了吧,噢,风格归我显示,风流归你发挥,是那么公平么?再说,给人家指点人生,那么有把握?误人子弟咋办?”
“吉,别那么认真。咱们不误她成都那帮也得误她,都差不多。人生茫茫,已然误入,再误何妨。来来,再给哥们儿切块萝卜;今儿这‘白毛猴’真不错,可惜光顾了说话了,这第三过儿才喝出味。”
24
连敲三个两下——还从没敲过自己小屋的门,这声很新鲜。小来拨开门闩,我后脚还没进去她早哧溜钻回被窝了。果然又一地烟头。桌上倒扣着几封封好的信和一个缎面笔记本。
“出去,出去,你的手太凉。”
“你给我焐焐不行?我大老远赶来。”
“活该。又不是没人给你焐!”
“小来,”我看了看日历,“要不我后天陪你一夜?”
“你陪她去吧。我又不是你老婆。你倒挺美的,白天一个,夜里一个。告诉你,我受够了。”
“你说让我怎么办?咱们这儿又不是阿拉伯又不是民国。我也想把你俩都娶了,可国法难容啊。要不我豁出去了,到时你俩轮着一三五二四六地去探视我。”我站起来,走到箱子跟前,“我告你我的存折在哪儿。”我忍着笑。
小来一笑,我就折回床头了。从被头下面那儿,冒出一股香暖之气,我把脸放在她的胸上,她的左乳发出“怦怦”的柔声,我不说话。她胡撸着我的头发,“你有好几根白头发了。”
“疼,别拔。那是想你想的,肯定是三十多根儿吧?正好是咱们分别的天数。其中最白的那十根,是接到你电报十天内长的。你为啥要提前11天发报呀?”
“我也不知道。恨你。想起去年在西藏饭店你那么蔑视我——”
“嘿,小迈现在怎么样?”我钻出脑袋。
“人家有男朋友了,你别惦记了。”说着,小来亲我,稍有点儿突然。又问,“你能喜欢我多长时间呢?”
我掰着十指,又凑起她的五指,假装算半天,放倒了12个手指。
“12年呀?”她摸着那12个手指,摇头。
我把立着的那三个手指伸到她眼前。
“三年,这还差不多。我想的也是两三年。”
我在她的胸脯上画一个问号。
“因为你就能活到四十岁。”她望我。
“你这丫头多自私呀。就因为我不能继续爱你了,你就咒我。”
“不是,你真的活不长,我感觉。”
“那我就死在你的怀里吧?”“你不是有好几个怀吗?”
“看看,瞧你这胸脯长得不小,里面的心眼儿怎跟耗子心眼儿似的?”我掀了掀被头,“不过也是,埋在哪个坟头不是埋?让我看看你这儿的坟头。”我重又把头埋向她的两胸之间。
“你死了怎么办?”
“那你好好养我的儿子呀。”
“你想要多少儿子——真要‘一炕’么?”
“我希望你俩一人至少给我生一个。”
她用鼻子哼一声。
“对不起,不是你给我生;是你想要儿子了,我义务帮你,是我给你还不行么?”我笑。
一小时后我们起来。不巧,有人敲门——映在门玻璃帘上的影子是个长发。小来冷冷地看着我。
进来的比小来漂亮。她俩互相打量着,都没忘了微笑。
“这是小来,川大的;这是小琛,外企的。”
小琛望着枕头,那上面有两个凹印。
刚才小琛敲门,并没等“请”就进来了。她坐下之前还把椅垫翻了过来,所以小来已用眼睛那么望过我两回了。
我过去放录音机,挑了一盘卡伦·卡彭特的。“你俩喜欢她吗?”她俩似点头似摇头。“你俩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?”她俩还是半点半摇头。“嘿,呆会咱们一起去‘辽阳春’吧?有秋季刚上的‘酸菜白肉’。”
“别紧张,斯健,”小琛拿起水杯就喝,喝了半口,“慢慢讲卡彭特是怎么死的。”她微笑地对小来转过脸,“你叫小来呀?不过我没听斯健说过你。”
“他也没跟我说过你。”小来脸也松了些。
“难道我新认识一个,就得到我所有认识的人那儿去注册么?”我见她俩都笑了,“我到你俩那儿也碰见过我不认识的人——不是姑娘。”
小来掐了我后背一下,但她没掐住,我后背净骨头。我出屋去洗萝卜,就听屋里发出笑声。还听见一句什么“萝卜人儿”。
午饭时她俩聊起出国、托福、签证的事。我插不上嘴,索性比较她们俩——很难有机会请上俩喜欢我的人同时吃饭:小来面部一般,只是眼睛里有一种狠劲;小琛五官细致,略像乖男孩儿,她的胸部就是我见过的最理想的。
“你俩怎么那么亲热?”
小琛抬起眼,“嫉妒了是不是?”
小来接道:“我俩打起来有你的好么?”
“来来来,咱们仨干杯——服务员,再拿两瓶啤酒。”
送走小琛,我跟小来去北海。两个钟头后,小来脸上的酒晕消了,话就少了。
地上一长一短两个影子,腿都显得特长。我忽然贴在她的身后让影子合二为一。她闪开了,脸上平淡。
“我不想在你的小屋住了。”她没看我,看着湖面。
“行。我那屋也太破了。你去住吉的另一套房子吧,你可以去吉那儿吃饭。”
“那你今晚就送我去。”
25
我敲半天门,叫了好几遍“小来”,门没动,我便去吉那儿了。
“没在是不是?你约好了吗?”吉问。
“约了。前天晚上我送她来,你也听见了。”
“昨天她还来这儿吃晚饭呢,没说她今天要出去。跟我聊得还挺高兴呢,一直到11点。是不是?小央。”小央点头,吉摇了摇头,“怎么着?斯健,没吵架吧?”
“我压根儿就不会跟姑娘吵架。”
“可你的冷落比吵还让她们恨你呢!”吉冲着小央,“你去买点儿馅饼。”见小央离开,便说,“是不是有别的姑娘撞上了?”
“小琛来了,可我们仨吃饭还挺高兴呢,她俩谈得跟二姨太三姨太似的。”
“这你就不懂女人了。什么叫面和心不和呀?这词儿八成就是从女人那来的。”
“可是小来怎么不特在乎我老婆呀?”
吉站起来:“你真木。”又坐下。“你老婆名正言顺,小来当然懂得师出无名;再说小来还没找到在乎的机会。小琛就不同了,跟小来一样,就是‘小’字辈的,当然得争了。”
“你都跟她聊什么了?”
“不是我一人,还有小央。聊什么?川菜川人呗。李劫人的《死水微澜》,那个谁的怪味剧本《潘金莲》,作曲的郭文景,画画的罗中立,还有刘晓庆、刘文彩,最后聊的力兄。她几次想让我谈你,我都转到你的优点上去了。对了,她这次所谓随团采访是她非要跟来,是自费。”
“我明天再来——我这骑车来回三十多公里呢。”
26
“她又没在吧?”吉一开门就问,“我昨晚饭后去她那儿,她正在跟几个邻居打麻将。桌上的钱都是十块一张的。我让那个邻居走,她还拦着,说玩得特来劲。我问她输了多少——她肯定输,那几个邻居都是老麻,肯定仨人抠她一个呢。我告她你明天来,她没说什么;我说你今儿来过,她也不说话。就是抽烟、出牌、递钱。那几个人都抽她的烟。”
“吉,这要有毒品她非去吸毒不可。”
“没那么严重。她有时的风格是有赌博的特点,不能愣劝;再说也该让她报复你几天了。你也不用天天往这儿跑了。呆会儿你写三张给她的条,签上今、明、后的日期,我一天去给你贴一张。她若看到你天天都来而不遇,锲而不舍,会动点儿心。”
“吉,那你贴时,小心她正上楼——那样,哥们儿可就一点儿戏没有了。算了吧,还是我每天来自己贴吧。不耗耗体力,我更难受。”
“那你活该吧。”吉一摊手。
“快给哥们儿削个萝卜,嗓子特难受。”
27
下午,有人敲我小屋门,敲了两遍“探戈”的点,我从没听过。我喊请进,门没动。
我一拉门:小来。
“真没想到是你;在这个门上,我从没听过你的敲门声;再说自己家门还用敲么?”趁着她笑,我把她横抱起来。
“我是怕万一打扰了你跟小琛小浅什么的。”
“我以为你出意外了呢。我正准备去急救中心和炮局找你呢。”见她笑到一半停下,“炮局就是总拘留所——在炮局胡同。”我把她放在床上,“快让我检查一下哪受伤了?”
她笑着搂我,一句也不解释。我发现她下眼睑有点儿颜色发深。她把我抱得很紧,使劲亲,好像三天没沾吃的了。
从下午四点到晚上11点她没怎么说话;从晚八点到11点我也话少。我们累了,双双眯了一觉。她睡得特甜却又不深,因为她半睡间还时而摸我一下。
“你该走了,都11点了。”她揪着我的胸脯。
“我今晚不走。”
“不。我嫌太挤。”她微笑着说。
“那我呆到12点吧。”
我俩静静躺着,好像在比谁能坚持沉默。
“是不是有时沉默特舒服?”
她点头。
她还不出声,我去搔她肋下。
她故意把胳膊张开。还顶着我的劲,以加强效果。
“死皮。”我捏起她肚子上的一层皮肤。
“别忘了,咱们是三年。”
她在空中画了一个“对勾”。
“三年之后我还想活。”
她闭上眼睛。
“万一我要喜欢你的时间持久呢?”我晃她。
她指指钟。
“万一钟都跑坏了,我对你的喜欢还没变?”
她还指钟,又加上了门。
“好吧,争取明天见。”我整理好衣服,拿起车钥匙,临出门又亲她,感觉到她的舌头比说话时还活泼。“今晚真好。”我推开门时说了这句话。
轻轻的一声“嘎噔”——屋里一下黑了。她拽灯绳的动作是她今晚最后一句哑语。
28
我除了上街吃饭,足不出户,就是出去吃饭,也大开着录音机;车钥匙扔在明显的位置上。
第四天晚饭回来,有张条。没抬头没落款。
“出租在等我,还有40分钟火车就开了。你要能追得上就来送我吧。”
录音机仍在响,只是磁带被谁翻过了面。
刚才那顿饭我喝了点儿酒,用了半个多小时。
我骑上车,到了西单路口。想了想,我向西拐,去了吉家。路上,红灯很多,仿佛那三个灯,只剩红的没坏。
29
五天后,小来来信:斯健,等检票时,我特怕你来,也特怕你来了就挽留我。刚一检完票,我站了半天,等着你出现,有几个人特像你,我都快喊了才发现不是。走上通道我多次回头。每一次都决心这是最后一次。你没有来。或者你来晚了。转告吉,没能跟他告别,还有小央,她是个好姑娘,好妻子;我不是也不会是。我喜欢吉说话,若能常跟他聊聊天,那真是舒服,他的知识比你丰富。我很高兴你有这样的朋友。对不起,我一直没能习惯你们的萝卜。这信是在火车上写的,得回到成都再发。我也不知回成都将要怎样。爱我的穷诗人有,想娶我的阔佬也有;父母还让我赴美;报社还让我毕业后就来。我打算一进家就先关门睡两天。祝你健康!小来。
发信前,我犹豫一下,还是寄给你吧。又及。
我复信:
小来,在你的信封里没有倒出你家的门钥匙,我知道你不是忘了。这两天我搞来一些舒曼的磁带,天天听。并打算托人捎给你。我可以托自己捎给你么?我没有去车站追你。去了吉家,“吃萝卜,就热茶”。吉说那天你输了二百多块钱,他问了那边的邻居。我们仍然写,稿费零星,有时也抽骆驼以下的烟。我很想你,甚至有点儿悲观。我不希望你和力兄好。我写了二十多个小笑话,都是咱俩的小事。附在信后。我喜欢你,还没到三年呢。这一点你也别忘了。祝你好!斯健。
十天后,我再致小来信:
来,我的小屋已生火,比你住的那几天暖和多了。破的窗户,也糊了新纸。我用写大字的宣纸糊的,挡风却透阳光。对面房脊上的鸽影能映在窗纸上,纯是线条。几只刚断奶的耗子,身子也就栗子那么大,在地板上乱跑,不特怕人,那小眼睛也是婴儿的目光。它们的鼠娘,大概是你刚到京那天受的孕。吉和小央都问候你,还说那几个邻居要把赢你的钱退你。你对我的态度就好像给合唱起了一个头:我老婆和小琛现在都不爱搭理我了。所以我的身体不得不像出家的僧人那么好。也祝你健康。斯健。
30
约半月后力兄来信:
斯健:小来一周前两次,未遂。第一次吃了200片安眠药;可能是,因为床头剩两个空瓶。被邻居发现后送医院急救。事隔两天,又服二百片,但第二天上午抢救后醒来,便割开手腕脉管,又被亲戚发现。她现已住进精神病院。谁都见不到她,除了小迈,我估计这和你有关,我觉得她不想真死。她从京回蓉后,我跟她聊过两次,没见异常,可见她隐忍之深。一有可能我争取见她。没想到你俩还真是爱得死去活来。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,我就不说你什么了。
我即刻致信小迈:
朋友中只有你能接近小来,你们最要好。请你看在咱们过去感情的份上告诉我:需不需要我马上赴蓉?需要钱吗?我能够做什么?小来的病型是什么?她现在身体和精神到底怎样?你若能劝导小来抛弃厌世的念头,我会感激你一辈子。一年多未联系,不知你地址变否?
但愿你能收到此信。
31
十多天后,力兄复信:
斯健,我们已去医院探视过小来,现在基本正常,还跟我们开玩笑呢。她和我们都没提你。医生说她是严重的抑郁症。她答应我们不再。在花园里散步时,她跟我说她不希望小迈知道她的事。大夫说她最多一个月就能出院了。但她表示想多住些日子。她说在家里休息不如在医院里。她的国内外亲戚来了不少,有的正在给她跑出国手续,她说无所谓。你若写信给她,不要说太多,别开玩笑。我会常去看她的,我也喜欢她。我最近没写诗,但还会写的。吉跟我的彻夜长谈,现在也让我感激。代我问他好。你的新作像历史白话文,大一时就读过。
我让力兄转信给小来:
来,我整理出一组新的诗,是你在京见我正写的《皇家猎场遗址》,大意讲:时间苍茫,朝代如水;再显赫的康乾盛世,再伟大的帝王,不过都是过眼云烟。所以,怎么活都是一辈子。力兄说我写的不是诗,是历史白话文,说他们读大一时就读过。在成都,我挤兑他的诗。我知道,他这不是报复。最近又出些散文随笔,容易换钱,写时也颇似休息,好玩。我身体越健康就越惦记你,怕你生病,怕你被人欺负,怕你抽烟过多。力兄善良而仗义,我挺感动。当面不好说,请你转告。祝好。健
32
又是周三了。今天倒是没什么西北风。
今儿骑得快了些,加上我小屋的钟可能快了,不到四点我就到了吉的楼下。我在楼下溜达到四点才上去敲门。
等了一会儿门才开。像每次一样,吉开门时在系着皮带,眼睛还没全亮起来。
我看看墙角:“心里美”还在网兜里系着。桌上是茶叶的纸盒铁盒,都是些名牌。
“又有新消息?”吉一边沏着茶,看完了水涨到杯沿儿,才把目光抬向我。
“没有。”我看看乌黑的茶叶在水中舒展开,“今儿是什么乌龙?”
“‘黄金桂’。你等会儿,我去洗萝卜——现在那个卖萝卜的‘眼镜’每天都挑几个好的给我留在网兜里,每天我都是中午下班去拿——”
“是不是跟每天取奶似的,特定时?吉,你说能不能造一种萝卜‘奶’,肯定价廉,省得人老得洗呀削皮呀怕糠呀。”我跟吉到了厨房,“贵人不吃贱萝卜,可喝萝卜‘奶’他们总不掉价吧。到那时,小来小琛她们,‘啪’一声打开易拉罐,就往嘴里倒萝卜汁——不,萝卜‘奶’,那多好玩。”
我俩回到屋里,吃口萝卜喝口茶。那种“嘎巴”咬下口萝卜的脆声和“嘘嘘”的喝茶声,充填着说话之间的沉默;萝卜声和茶声反而使沉默更加清晰。
“吉,咱们在小来那儿算完蛋了。”
“把那个‘们’去掉。”
“你不是也给她讲过人生之道吗?讲的总不是人死之道吧?我不相信她是为了区区爱情——她不会干这种俗事。”
“斯健,你的意思她是:朝不闻道,夕死可矣。若真这样,她可比闻道而死的人还超脱呀。‘道’算什么东西,还得等到明早知道;这种等太无聊了,算了,不等了,今晚就死吧。等那个‘道’时的无聊程度可能比得到那个‘道’时的幸福程度厉害多了。”
“也是,知‘道’了再死,与不知‘道’而死,在这死之后有何不同呢?就算未来能研究出哪种不同,于那个死者又有什么用呢?”
吉给我续水,“越说越晕——你觉出来了么?现在萝卜不如十年前的好吃;个儿倒都不小;全是化肥催的。”
“没错,十年前的姑娘多纯朴啊。要就为爱而死,那多豁亮。为‘我有迷魂招不得’而这可真他妈的变态,都是那些现代艺术,对了,就跟化肥一样,把人给催得‘走向深刻’。‘深刻’那玩意儿哪能是个人就能担待呀。”
“怎么又绕回来了,别老惦着小来的事啦。”吉又喝了口茶,不咽,在嘴里来回漱,呼呼作响,好像要把嘴里的萝卜末一点不剩地“营养”到肚子里。“咕咚”一声之后,吉张开了嘴:“斯健,你也是替小来瞎操心,她不是被救过来了吗?不是快去美国了么?你放心,‘抑郁症’虽然行为极端,但并不难治——我查过精神病学。并且很多文学、艺术、哲学大师,都有这毛病——就跟天才的特点似的。”
“咱俩这辈子怎么也不会成为大师了。”我接道,“压根儿也不忧郁——先天素质不足。”
“我高中那会儿,就快到‘忧郁’的边上了。”吉也来了精神,“要是及时看看梵高的画、蒙克的画什么的,听听老柴的‘第六’、老贝的‘第五’什么的,估计也就忧郁成功了。可是——”吉正在想,但手势已经展开了。
“你老吃萝卜。”我一边指着。
“唉——结果,那种‘准忧郁’慢慢消失了。现在是彻底没了,再听谁的音乐,看谁的画,再碰上什么事也不会忧郁;最多就是忧伤吧,也不是,是不高兴;比如丢了钱失了恋什么的。斯健,你这几天是不是想学‘忧郁’了?”
“不至于,咱这种打萝卜嗝的人要是也忧郁,那么忧郁还有啥价值呢。”
“斯健,我给你讲,小来有忧郁的素质,又经历过生死关头,再加上你教给她的一些有用的‘俗’,她可能成就一番呢——对了,她还能去美国,父母有钱,不用为生计操心。我看你以后别给她写信了,各安天命吧。她吃她的美国苹果,你咀你的中国萝卜——来来,再吃两块,都给它吃了算了。”说着,吉把桌上的几块萝卜用手从中间一分,然后带头拿了一块。
萝卜皮已经一地了:一片儿一片儿的,像新鲜的树叶。窗外,杨树杈光秃秃的,一点儿不晃。
“那你重新给我沏一杯。”我端起杯给他看,“哥们儿这茶都没色儿了。”
(插图 库雪明)
相关文章:
《美人册》之一
《美人册》之二
《美人册》之三
《美人册》之四
《美人册》之五
《美人册》之六
后小组简历 之一
后小组简历 之二
后小组简历 之三
后小组简历 之四
后小组简历 之五
啤酒主义宗师:阿坚 | 宁导眼中的阿坚
诗人·阿坚——写给一代无产者
阿坚的信(21封)
陈教授新语(2005至2016年)之一 | 大踏
三位有情
回忆八五班——拼不成形的一些片段
七夕
海豚音
北京千米以上山峰词典(一)
北京千米以上山峰词典(二)
北京千米以上山峰词典(三)
北京千米以上山峰词典(四)
北京千米以上山峰词典(五)
北京千米以上山峰词典(六)
北京千米以上山峰词典(七)
北京千米以上山峰词典(八)
点击下方 阅读原文 链接可进入西局书局书店,购买(免邮费)首届西局书局奖获奖作品《闭嘴》及其他优质图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