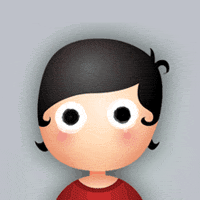诗人馀秀华的故事
本文由 自强新闻 出品并授权转载
4月2号,余秀华更新了微博。
“海子”。
三首纪念海子的诗歌。
在其中一首《遇见海子》中,她写到,“这个孤独的孩子自言自语,走出人群/多少年过去,一种怀念不断消散/我们的亲近来自同样的血液,不是a,b,ab,也不是o”。
海子=孩子?
主题是:我曾经那么爱过他。
在一个海子忌日过去整整一周的时间。诗人余秀华与历史擦肩而过。
身为“女人”、“农民”、“诗人”的余秀华,是以“脑瘫”、“农民”、“诗人”的符号走红的。
2014年9月,《诗刊》“双子星座”栏目,刊发了余秀华的一组诗。
11月10日,公众号“诗刊社”,发“摇摇晃晃的人间—一位脑瘫患者的诗”一文。
12月17日,余秀华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小型非个人朗诵会。
12月22日,,随后,、央视等媒体先后发出余秀华报道。余秀华更深一步地走向大众。
2015年1月13日,旅美学者、女权主义者沈睿发表博文《什么是诗歌?余秀华——这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》,称其为“中国的狄金森”(她回应说,“我不认识她”)。此文被冠以标题“余秀华: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”,被网友疯狂转发。
还有出现在标题的那首诗歌。。在后来的访谈中,余秀华坦白,“我也不知道《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为什么火,那并不是一首好诗,只是有点标题党。”
这一“文化事件”持续升温,媒体跟进采访,诸如南方都市报、澎湃新闻。在余秀华家,那个院子,横店村,“记者一到,兔子就死。”面对记者采访,她坦诚,胜过孩子,胜过“如果你将她比作一个孩子”。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交流,是一遭问题与答案的甜蜜邂逅。当然,客人不期而至,络绎不绝,官员(政府、文联、残联)、诗人、粉丝、出版商、保险业务员、民间组织人士。
她在湖畔朗读《我爱你》,这是她第一次面对公众用声音绘画。“巴巴地活着,每天打水,煮饭,按时吃药……”声质与一只旧收音机仿佛。一分半分的朴实的泥土味。
1月28日,余秀华当选为钟祥市作协副主席,在本人未出席的情况下。她“不需要任何人特别是官方的肯定。”
2月,湖南文艺出版社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分别出版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、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。这是诞生在超速生产线上的商品。前者或后者,“海子之后,最畅销的诗集之一”。两者都是。
2015年12月,婚姻破裂。
公众号“凤凰读书”有了“余秀华专栏”。2月24号,第二期。她说,“我一直以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,人的出生是暂时和自然隔离开来,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用一辈子走回到自然里去。如果认识了这些,一个人再怎么高调也是有限度的高调,温暖的高调。”她转行做起了评论家?文化学者?
时至今日,余秀华奔波各地,做签售后是忙讲座,讲“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,诗充当了一根拐杖”。她说,悲苦未减,欢乐见增。
诗人余秀华的童年是“灰色的”,因为“先天性脑瘫”。这个理由是充足的,因为生命开始于身体;她是“一棵稗子”。不过,在余秀华的诗集中,“身体”一词是常见的,作为一个隐喻,“身体”化作“容器”,是生孕物质实体的母体,“灵魂”一词寥寥,“生命”一词却是几乎未出现过的。
这颗“无名星”,自己生产着“胎记”。
高二辍学。
辍学后,她坐守一家小卖部,在生活的一边是:宋词,《知音》,象棋。也许还有“诗的影子”。
1995年,余秀华女士结婚。父亲为女儿招婿。她说,“青春给了一段罪恶”。
生子。
2005年的一天,一张写着扭曲的“分行的字”的纸,开始了专属于它的一段短期旅行。信封有去无回。邮差回来了,撂下一期《钟祥日报》,有的证据指向了《九月》。
2008年,她“蘸着身体”写诗歌,这诗歌已然是网络的产儿。她在“云端梦呓”。
有时,诗是“丑”、“凶蛮”、“污俗”,是“反”。成名前的岁月在阳光中暴晒;它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声名不仅过于平淡,还是假象。
后来,“天上掉了馅饼”,他们说。他也说。
“这只是一时的,并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,很快就会过去。”类似的话在几乎每一个采访中都会被重申。
诗歌不变。她说,“诗歌是不会变的”。
那我们就忘掉她雾一般的身份,将眼睛和思想聚焦在这句子上吧。
“瞧!”:
“一年里,秋天是最具备植物性的。”
“村庄不停地黄”
“蛙鸣漫上来,我的鞋底还没有磕出的幸福/这幸福是一个俗气的农妇怀抱的新麦的味道,忍冬花的味道/和睡衣上残留的阳光的味道”
“小小的雷霆和火焰/在风里摇晃”
“一些光永远隐匿,在原野上保持站立”
“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,它已经老了,无力回天了/许多部位交换着疼:胃,胳膊,腿,手指”
“肉体落定下来,灵魂还在打转”
“那时候,我不用回头,总相信/你一直在我身后”
“女人心意已决,但是无法开口”
“我钟爱的这个时辰把一个世界呈现在我面前,此刻的世界是一种温柔的性质:山吐风微蓝,水吐出的蓝稍微淡一些,它们在巨大的交融里有一些微小的对抗,这迷人的对抗里呼哨尖刻,但是这样的尖刻其实抓不住的。抓不住也说不出来,一说就错。而我偏偏沉迷于这些无法获得的错误。”
真诚。乡居生活。美。你大概会罗列类似的词。
这时,我仅仅将自己看作一个读者。我拨开那一排灌木屏障,穿行在洒金紫阳光的小片森林,有时仅仅为听到一个声音,捕捉一个符号。
她宠爱“春天”、“雪”、“月光”、“风”、“当归”、“烟灰”、“打开”、“按”、“磕”、“白”、“疼”。感情在重复使用中生成,纯化。
诗中很少、甚至从未出现“夏”、“夏季”,只有一次,“比起夏天,青草的声音迟缓多了”。
诗人不局限于使用词汇。使用是重复词汇的既有定义。诗人需要是新的定义,是词汇的源头,它的原始定义,一个内在的定义。
诗歌是语言精粹。诗歌不局限于词汇。词汇是既成的,以知识的形式,为我们习得。语言则是偶然的,它不仅在知识中游动,也在观念意识精神中游动,在诗歌中,语言是“因”,是词汇之源,万物之因。
她偏爱形容词、副词。它们生长在诗句的草丛,探出明亮的花絮。它们被动词化。
对于意象的经营,诗人不甚在意。也许是因为经验少,意象局限于固定的几个。也许是因为,诗歌是艺术品,这要求精耕细作。
有时,诗人与意象互动。有时,诗是意象的隐形的主宰。
在《背景》这一首诗中,诗人惯用的意象几乎全数登场:
数场雨,一棵树单薄了
太阳出来了,照着那些发暗生霉的叶子
真不招人喜欢了。
这么蓝的天扣在横店村的上面
这么白的云浮在白杨树的上面
新种的小麦晃出一层毛茸茸的绿
野草枯黄出让人心醉的时辰
我坐在田头,秋风都往怀里吹
麻雀儿一阵阵的,落下又旋起
它们落在横过麦田的电话线上,那么轻
不忍惊动远方传来的零星的消息
一些意象和语境是“偷来的月光”。
看看这句,“我也想起‘雨’,总会让时辰更为明亮”。似乎与博尔赫斯的“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”(出自《雨》)有几分相似之处。“也”不正是借鉴之意吗?
难道“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/喂马劈柴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”不是“巴巴地活着,每天打水,煮饭,按时吃药”的先声吗?
还有“我的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”。等等。
有时,她用“错”词,将组合打散;突然,整个句子看起来如此不合乎规则。又或者,句意的光彩太强,削减了诗意。
她的叙事诗,有那么一两首简直是畅达、和缓得过了头了。诗歌的“叙事性”,从一个区到另一区,联系词汇,沟通意蕴,如同“语言河流——这肉嘟嘟的水”。
谁会否定呢,如果你说,“遣词造句、构象拟意上,她进驻了‘诗人圈’”!
无数次,诗句呈出“倾斜”、“摇摇晃晃”,这是被洗净的果实。摇晃着的不是身体,是灵魂,是住在身体居室里的灵魂。
“诗歌净化……”,她说。诗歌淡化了身体存在的迹象,灵魂为她描了一道金边,一个“赋义”的轮廓。
身体是属于空间的限制。人在时间中延绵。不仅是想象,还要是“理性的想象”。
面对身体所象征的“难”,诗人控告;却局限于“我”,失却呼应,失却对象。她要对话,但又明了对象是不存在的,明了对话终究只是“独语”。那些个浅诗,陋诗,可以看作是诗人对内在的“对话”欲望的体察与讥讽。
诗,弃“解”;诗原不求解。
诗人余秀华是有着异域气质的。她的诗歌不同于一些本土诗人的诗歌,它们往往是驳杂的,像一张施展开的捕鱼网。余秀华的诗歌则更像是一只鱼缸,你窥见它,便有你个人的美感,是个体的精致,像一些古典诗歌,像一些译诗呈现的那样,而不是集体的“大美”。
总之,诗歌是“她的解释”,而她正需要这样的解释。诗歌存在于她,并与之达成某种和谐。
历史会不会说,“这个时代的诗歌是畸形的诗歌”?
上世纪80年代是诗的年代。
苏醒。改革开放初期。“市场”、“大众传媒”的缺席。理想主义。
“诗的生态”。
诗自然。
诗生根发芽。
在“商业”、“媒舆”,“实用”、“功利”的狂风暴雨下,诗“暗下来”,“败下去”。
海子把诗一整个儿地打包带到天堂去了!
批评家说,诗歌与公共生活产生了陌生感。
诗人强调个人写作,看重个人情感的表达
诗有点像是一门手艺。诗人奔走于酒吧、茶设社、沙龙和诗会,做生活的观光客。诗歌是类似于壁挂、灯饰、木雕的工艺品。
诗不再是“原始”,不再是“神圣的高贵”。
诗,借助其他工具,重获它的权威。
大众可以是权威。于是诗歌伪装成大众艺术,媚俗因素渗入生命的真实。权威在体制之外,读者群拿着权威金杖。
权威是诗人的?因为:诗歌是个体的语言,个体的美。
若诗歌的权威归还于诗歌又会如何呢?
回到诗人余秀华。
“我用我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,最大力气左手压右腕,然后将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。字留下来……”
“于我而言,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,我才是完整的,安静的,快乐的。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安静的人,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,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,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,我会泼妇骂街……”
认真活着。“只要我认真地活着,我的诗歌就有认真出来的光泽……”
“一直深信,一个人在天地间,与一些事情产生密切的联系,再产生深沉的爱,以致无法割舍,这是一种宿命……”
她说:“诗歌是灵魂的自然流露。”
而后,她踌躇说:“灵魂是什么呢?”
“长江的水在呜咽,我尚在武昌/长江的水在呜咽,我在长江上/长江的水在呜咽,过汉川,过京山/长江水在呜咽啊,我在横店村//横店村,它可是我家乡?/为何我的亲人都散落在远方?”(《别武汉》 2015年1月28日)
“今夜我不想一个人/这一次漂泊里,我离他离得/这么近”(《今夜我在武昌城》 2015年6月3日)
她来了,在另一个时间离开这儿。
“她的芬芳要求领悟,要求你在稠密的利刺间/找到发光的箴言”。